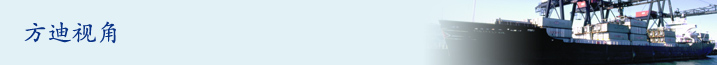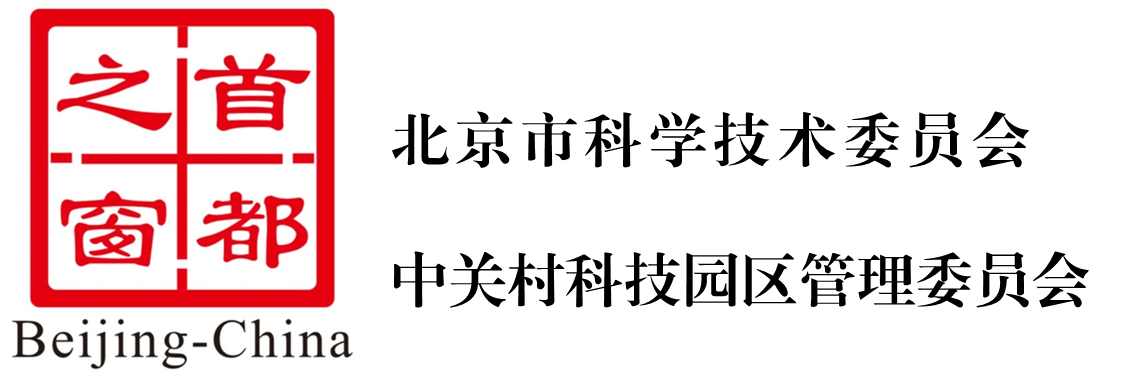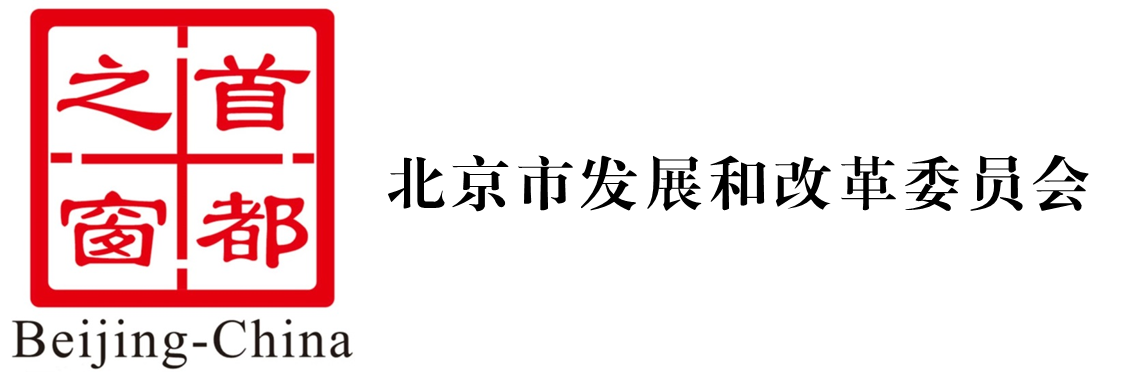| 站内搜索: |
|
方迪视角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
业务咨询:010-58572828 办公室:010-58572826 传真:010-58572827 电子邮箱:zbjjlt@126.com 联系人:王女士 邮编:100120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乙6号京版大厦B座13层 |
北京中心城人口与功能疏散的国际经验借鉴添加时间:2010/12/08作者:赵秀池 刘欣葵来源:商业时代
北京市中心城功能和人口分布现状分析
(一)北京市人口疏散的目标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2020年北京市人口分布目标为:中心城人口规划控制在850万人以内,新城人口约570万人。其中旧城人口约110万人。即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现在的180万人降低到110万人,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新城人口由现在的220万人增加到570万人,其中三个重点新城(通州、顺义、亦庄)达到270万人,中心城与新城之间人口分布比例由近现状的4:1降低为1.5:1。通州、顺义、亦庄新城规划人口规模为70万—90万人;大兴、昌平、房山新城规划人口规模约60万人;其它新城规划人口规模在15—35万人之间。 (二)北京市人口增长及分布特点 1.北京市人口规模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到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从1538万人增长到1633万,年均增长率为3%。其中户籍人口从1162.9万人增长到1213.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4%。外来人口从358万人增长到419.7万人,年均增长率为7.8%。外来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是人口规模总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2.外来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这一比例在1990年约为1:4,2000年增长到1:3.7,2005年继续增长到1:3.3,2007年继续增长到1:2.89。 根据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的数据,截止2007年底,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419.7万人,其中分布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37.5万人,占全市外来人口的8.93%。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242.5万人,占57.78%,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122.3万人,占29.14%,门头沟、怀柔、平谷、密云、延庆17.4万人,占4.15%。目前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五个新城成为新增外来人口的主要承接地。 3.城区人口密度高于平均密度。以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分项来统计,城市人口密度逐级下降,出现级别分明的四级结构。2006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为206.1万人,常住人口密度为22308人/平方公里;城市功能拓展区2006年常住人口为773.6万人,常住人口密度为6063人/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新区常住人口为424.7万人,常住人口密度为675人/平方公里;生态涵养发展区常住人口为176.6万人,常住人口密度为202人/平方公里。北京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最大,是城市功能拓展区的3.68倍,是城市发展新区的33倍,是生态涵养发展区的110.44倍。 (三) 北京市中心城功能疏解现状分析 目前中心城功能疏解刚刚起步,势头较好,中心城功能疏解通过项目带动、企业先行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顺义新国展、通州商务园、昌平科研基地,通州出版交易中心、亦庄中冶京城、延庆建院工作室、怀柔中科院研究生院等项目,在区县政府的重点政策支持下,已初见成效。但一些行政办公、医疗等设施向新城搬迁受阻。如通州作为行政办公的补充配套区尚未有相关部门提出搬迁意向,中心城大型医疗设施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宣武医院、儿童医院扩建多采取了原地扩建或收购周边设施的方式,还有的医院在中心城外围地区新建,未搬迁到新城。中心城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行了搬迁整治,相关物流设施规划用地调整到新城,但鉴于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水平,小商品批发市场难以在新城成长,如良乡物流产业园区等因物流产业发展滞后而建设滞后。 国外中心城人口及功能疏解经验借鉴 自19世纪开始,新城建设是世界发达大城市应对人口增长与城市无序蔓延矛盾的共同选择。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和香港等国际发达城市先后建成一批规模不一的新城,构建起由中心城市与新城共同构成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成为人口增长、新型产业和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区。经过新城建设,大巴黎人口空间分布出现了较大变化,距离市区中心10公里地区内的人口数大幅降低,而10至50平方公里内人数则有较大幅度增长。中国香港则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港岛总人口700万人,有300万人居住在新城。 自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完成城市化之后,城市发展开始以外延扩展为主。1950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的59%在中心城市,41%在郊区,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正好反了过来,60%人口在郊区,40%人口在中心城市。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一度出现“回到城市”的趋势,但总的看来,前往郊区的人仍多于回到城市的人。 分析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中心城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1940年之前,中心城作为人口居住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场所,其繁荣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投资和移民,但其负面影响日益彰显,不仅居住人口拥挤、交通堵塞,而且民族结构因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变得日益庞杂,社会贫富的两极化刺激了贫民区的膨胀,贫困与社会犯罪问题丛生。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政府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在城市进行大规模投资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进一步加大了对城市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和其它城市服务的需求。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城市住房已经达到饱和或超负荷状态。“二战”后,又有成千上万的黑人从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纷纷来到全国各地城市,大批拉美裔移民及亚洲移民纷至沓来,其中下层劳工就业难度大,失业率高,再加上白人的种族歧视,出现了美国历史上遍及全国的种族暴乱。在这种形势下,郊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政府政策支持使居住与工作在郊区成为可能。 美国成功实现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疏解的主要措施有: 制造业、零售业向郊区大规模迁移。郊区成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大本营,中心城市逐渐“空心化”。据统计,196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的67%集中在中心城市,但到1980年,下降为25.8%;1992年,每1000美元零售业所得中郊区占728美元,中心城市只占272美元,从1982年到1992年10年间,8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郊区在零售业所占比例增长了77%。 郊区居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居民。在美国历史上,城市居民的收入一向高于郊区居民,直至1960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还高于郊区居民5个百分点,但到1973年,这一比例倒了过来,城市居民收入低于郊区4个百分点,1980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1个百分点,1989年再达到17.5个百分点。1990年,大都市区人口中有60%住在中心城区,40%在郊区,中心城市的贫困率为18%,而郊区仅为8%。中心城区居民的平均收入远低于郊区。 郊区拥有优越的教育、社会福利、文化设施、交通等基础设施。以教育为例,无论是师资质量和教学手段,还是图书资料和设备等,中心城市远逊于郊区。1994年,纽约市郊区平均每年为每个学生支出达9688美元,而中心城市为8205美元;郊区学校平均每名学生配备的图书数量平均为20本,中心城市为9.4本。1996年,59%的郊区学生可上互联网,中心城市的比例只有47%。 郊区风景秀丽、住房阔绰。在郊区风景秀丽的地方,拥有一套独立而阔绰的住房,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纷扰,安享恬静舒适的生活,是美国梦的象征,也是白人中产阶级逃避城市问题的避风港。 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国会曾多次颁布法案,加强城市公路的建设。高速公路的建设缓解了城市交通拥挤的窘况,为居民和产业脱离中心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在“二战”期间,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一些大型飞机制造公司、军火工厂、飞机场和军营等以现代化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国防工业从一开始就落户在郊区,为日后吸引更多的民营工业投资奠定了基础。战后,联邦政府仍继续实施偏袒郊区、抑制中心城市发展的政策。 北京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疏解对策 (一)加大北京中心城区向外的推力 1.通过建设新城截留旧城人口,实现增量人口进新城,存量人口在旧城。通过新城开发建设,带动人口到新城的转移,实现增量在新城,存量在旧城,通过新城截留旧城人口,达到疏解中心城人口的目的。 西方发达大城市建设新城时,城市发展基本上进入了郊区化的阶段,内城基本建成。而北京的城市化虽然出现了郊区化的态势,但并未成为主导趋势,中心城的集聚力远大于郊区的吸引力。中心城依旧是城市规划建设的热点地区,制约了中心城人口和功能的转移,因此要严格控制旧城的开发建设。 2.注重完善区域城市功能,实现中心城与新城的功能对接。一是促进新城功能与中心城的对接。北京中心城的主要功能是国家政治中心、国家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和服务全国的其他功能。其中,前四个中心的配套设施可部分向新城转移,如国际交往配套设施、金融后台等。教育科研中心和服务全国与区域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以及人口承载等功能应全面向新城转移。二是促进新城与中心城相关区域的功能对接。以朝阳CBD、海淀中关村、西城金融街等区域核心功能为区域中心,研究与通州、顺义、亦庄、昌平、大兴、房山(良乡)新城的居住功能和产业功能对接,促进区域居住和产业功能的平衡。 3.要控制中心城的建设速度及密度,保持中心城房价适当高位。要严格控制旧城的开发改造,限制中心城建设的容积率,保持一定数量的待改造和发展地区。要抑制旧城各区开发冲动,通过降低中心城建设的规模和容积率,以减少中心城的就业人口,提高环境质量。同时保持中心城房地产价格的适当高位,会促使部分企业外迁,促使一部分居民到新城购房,这样起到新城“截留”人口的作用,达到人口存量在旧城、增量进新城的目的。 (二)增强新城的吸引力 1.政府主导配置重大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促进新城实现规划功能。根据各新城的功能定位,市政府应统筹重大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的配置。当新城与中心城发生竞争时,应优先安排新城建设,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提高新城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新城实现其规划功能。 2.以住房政策和产业政策为重点,促进新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住房政策是国外新城建设成功的关键。住房也是控制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硬约束。研究制定居业联动的住房资助政策,使新城居民能够通过较低的价格买到较高品质的住房,吸引鼓励性产业、亟需的优秀人才(教师、医生等)迁入新城。 3.加大新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新城。高标准规划和建设新城社会设施。按照不低于中心城社会事业建设标准,新建和改扩建一批新城社会设施。新城学校、医院等社会设施的人均建设用地和建筑指标、抗震、节能、绿化等方面的标准应不低于中心城。 4.降低远郊区县生活成本,提高远郊区县生活便利程度。目前阻碍人口大规模流向郊区的主要障碍是郊区的生活成本高于市区,而生活便利程度低于市区。建议市政府从城市长远发展利益出发,重视远郊区县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具有现代城市文化特色的人文环境建设,增强郊区的综合吸引力。应本着“同质同价”“适当优惠”原则对新城区居民收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交通市政设施的服务费用。目前,郊区的公交线路收费比市区高,建议郊区的公交线路与市区的公交线路采取一个价格。 |